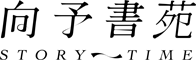※2022年蘭陽文學獎散文組 第三名
夏日獨自在家的午後,我總喜歡坐在臨窗的書桌。
窗簾在尋常的日子是緊閉拉上的,拉開後不免揚起一陣灰塵,日光不算太烈,卻也足夠將飛塵照得清晰。此時,我打開角落那檯稍嫌老舊的、餐廳才會看到的站立式大冷氣,轟鳴的風聲足夠把一切掩蓋,為我建造一個安全的泡泡。這時候,應該去冰箱拿出新買的冰棒,撕開包裝讓甜味在舌尖上蔓延開來,檸檬是沁涼的,焦糖是甜蜜的。
像是某種銘刻效應,那台站立式大冷氣,成為了我的家,成為哺育我的地方。
在轟然的風聲旁邊,我拿起手機,趴在冰涼的玻璃書桌上吃冰棒,打開還沒看完的影集,笑得歇斯底里或因為劇情眼眶泛紅,都不會有人評論。那幾個片刻,所有的煩惱、憂慮、期待與失望都可以被拋在腦後,不被定義或拘束,也不用去想遙遠的未來以後,可以允許自己稍微沉溺在此刻的快樂。這一刻,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自己活著。感受自己有明天可以期待,像綿延萬里的陽光,充滿希望而看不見盡頭。
這是我對家最美好的想像了:一個能擁有自己空間的小小世界。即便這個景象,從未在宜蘭發生過。
相信大多數人應該會對此感到意外,「家」在我們的觀念裡,往往與溫馨的大團圓、飯桌上滿滿的菜色相連,它應當與人、溫暖、愛意相關,或至少與土地相關——自我介紹時脫口而出的我是某某地人,是對家鄉最直覺的下意識反應了。
然而,我並無法用這樣的標準來定義「家」。
以生長茁壯之處定義,我會說自己來自花蓮;以有家人的所在定義,宜花二處都有我的至親。兩地都對我有特殊的意義,我這一生從最初開始,就與它們緊密相連,一時要追根究柢,剖開心問自己何方是家?我竟也給不出確切答案,只能閉上眼睛,描繪出一楨我記憶裡最悠然的畫面,告訴你,在我所夢想裡的家裡,沒有任何事物會被框架。
縱然,現實往往並不這麼美好。
說來也怪,我與宜蘭的關係理應親密,畢竟是我父母居住的地方,可整個成長歷程,我與它的感情卻始終不溫不火。一個月固定一次的造訪,像例行公事那樣坐著火車搖搖晃晃一個小時,去過短短的周末,隔天傍晚再搖搖晃晃回到花蓮,回到我求學的地方,回到我從三歲開始成長的地方。因此,宜蘭之於我,大概就像班上那幾個不太熟的同學,你並不討厭他,甚至有些好感,然而缺少了共同點的催化和相處時間,對彼此的瞭解僅止於班排成績或生日的一句祝賀。彼此也許稱得上一句好同學,卻怎麼也開不了口說是「朋友」。
若要深究原因,大概是因為宜蘭沒有站立式冷氣吧?
每月一次,火車到宜蘭的時候通常是一兩點的午後,陽光正烈,在計程車灰濛濛的車窗上反射出刺眼的星芒。我和奶奶把後背包抱在胸前擠上後座,和司機說了目的地之後,不可避免的是一陣沉默。轎車裡只剩下冷氣出風的聲音、跳表計價的機械聲,世界的喧鬧與嘈雜都被隔絕在玻璃外,壓抑著鑽入我的耳裡。
安靜並不難堪,我甚至享受這樣的片刻,可以拋開角色和思緒,淨空腦袋變回剛出生的嬰兒。
——偏偏世事不如人願,爺爺總會在這時打破沉默,談起昨天下了大雨或晚上越來越冷之類,奶奶則隨後補上幾句抱怨(對世事的抱怨,大概已深深刻在人類基因序列裡了吧?我常想天氣存在的意義,是否便是讓人有個可愛可憎又無害的共同敵人,使我們隨時可以向陌生人聊上幾句)就這樣,和司機你來我往,硬是要把三五分鐘不到的車程塞得滿滿當當。
這時候,我雖是聽著,卻又不像在「聽」——如果讓那些聲音飄進右耳,再輕飄飄的被冷氣吹走也算是聽的話——那是種很奇怪的感覺,我是坐在車裡的,冷氣溫度很舒適,抱著背包的姿勢也讓人很有安全感,窗外城市午後繁榮的景象掠過我眼底,卻也只是掠過。這就是宜蘭的景色,這就是宜蘭的溫度,每個月循環一次,不太留下深刻的痕跡。
在那一刻,我深刻感知到自己無法從軀殼裡抽離,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角色,我看到的感受到的都來自於主觀,並且只能像工廠輸送帶上的產品,任由時間推著自己往前走,去下一站,長大工作活下去,最後以某種方式死亡。有幾個思索的瞬間,我會對自己是否活著這件事感到徬徨,懷疑所擁有的一切的意義何在。
但這樣的狀態並不會持續太久。
我強迫自己從想像裡抽離,回到真實人生,計程車差不多也在這時停下,我禮貌地說謝謝,打開門走進燥熱的空氣中,車水馬龍的聲音再次隨著熱氣灌進我的感官,溫度的衝擊才會把我拖回現實世界。
好想念花蓮那檯站立式冷氣,我心想。雖然它明明那麼那麼的吵雜。
吵雜給人的感受很極端,喜或惡都清晰明白。我厭惡無法控制的人群,吵嚷混亂讓我有種下一秒就要暴動的錯覺,尤其是在學校裡,太過大的噪音常與責備、罰站、悔過書相連。不過我卻不討厭站立式冷氣機的轟鳴聲,那也一樣強烈,卻不會讓我驚慌無措,因為我知道那是我為數不多能掌控的東西之一,轉動旋鈕,我就是這小小世界的主人,我完全自由。
左邊是冷,右邊是熱,還要先調送風幾分鐘後再轉到冷氣模式——我對它簡直瞭若指掌,也正是因為這樣,我才能為自己製造出一座暫時的城牆,把世界都隔絕在外。想哭的話,就把旋鈕轉到最左邊吧,用極端的冷來麻痺腦海裡試圖理性分析的聲音,頭腦和思緒都變成黏膩的膠水等到緩和一點,想冷靜的話就關掉冷氣,恢復溫暖的空氣可以幫被壓制得那一半自己解凍;想沉溺一下的話,就調扇葉讓風直吹吧,風那麼強,可以吹乾眼淚和鼻涕,也可以把脆弱的偽裝吹散。
我的情緒常常在書桌前劇烈變動,高興到尖叫的大晴天會突然變成積聚的烏雲,但有站立式冷氣的日子裡,我卻很安心,因為我知道它可以摀住我的耳朵,把外界調成靜音,讓我默默破碎後重建,而不需忍受外界的眼光。
是啊,如果站立式冷氣機對我來說是家一樣的存在,那宜蘭大概就是精緻的變頻冷氣,而我是坐在風口底下的人,冷氣如此安靜,顯得我太吵,無處安放自己。
久而久之,宜蘭就這麼成為我最熟悉,也是最陌生的地方。
放長假時,我常會到宜蘭參加營隊,通常選擇年齡層廣的運動類型:羽球、熱舞、籃球。我可以說是運動中心的常客,在這裡,所有的友誼都是萍水相逢,彼此的人生像是兩條平行星軌,在這裡短暫交會三天或五天,淺淺的在對方生命中留下痕跡,便不會再有交集。
也許是這樣「期間限定」帶來的新奇,營隊眾人經常跨過小心翼翼試探的時刻,直接打成一片。我們可能不知道對方喜歡吃什麼、討厭怎樣的人、家裡有誰,但因為早就預測到了結局,所以快樂和氣憤都可以更真心,不用理解也可以。
我知道營隊結束的時刻終會到來,因此更加恣意享受了每分每秒的快樂,不需要日久天長更不需要永遠,就算都不會再相見也沒關係,至少那些鮮明的情感和球場上的吶喊一起,成為了我日後回想起時,會嘴角上揚的回憶。
這就是宜蘭啊。
回到熟悉的花蓮,交友關係就不一樣了。國中生的圈子很小,小到隨便一個同學都可能是摯友的學妹,小到我們之間緊密相連。因為熟悉,所以關係得要長期經營,慢慢認識、慢慢接近,小心翼翼的延續話題、了解對方。我們可能沒有一起瘋狂尖叫過,但一定會從考試成績了解對方的長處與缺陷、從日常對話裡逐間熟悉,或著在某次小組合作裡發覺對方可愛或可恨的地方。
仔細盤算,我到現在為止七年的求學生涯,生活裡總有些每一幕都參與的固定人馬;我記不清自己是在哪個時刻和他們真正成為朋友——失落時遞上的衛生紙、分著吃的一片蛋糕,或某次燥熱的放學不得不同行的十分鐘——但我能確定的是,我們的感情會持續加溫。
簡而言之,若說在宜蘭的友誼是大火快炒,喜怒哀樂都分明,花蓮的友誼就是小火慢燉,緩慢的親近,然後就是以年為單位計算的時光。
啊,對了,不曉得你是否知道,花蓮和宜蘭都有大型百貨公司,巧的是名字也都是四個字。
爸媽在宜蘭的家,位於新月百貨附近,在我僅知的幾個地點裡,它是我數一數二常去的地方。假日晚上的人通常很多,但卻不壅擠。這裡有許多花蓮沒有的服飾店、餐廳、電影院,販售的一切和空氣的氣息都讓我感到陌生,我行走在店與店之間,看著琳琅滿目的商品,常常有種巨大的陌生感。
倒是,花蓮的百貨公司就不一樣了。
小的時候我在遠東百貨參加寶寶爬行比賽,在童裝店裡穿著紗裙轉圈,再大一點開始溜直排輪後,廣場前成了我和同學盡情呼喊的地方,如今我依然會在假日時央求家人帶我去那裡,走過爛熟於心的樓層,我幾乎可以背出下一間店的名稱,偶爾看見相同的櫃台人員,還會在心裡偷偷和他打聲招呼。
宜蘭帶給我的是感官上全新的衝擊,而花蓮,則讓我能在安心的所在中,探索新的可能。關於家的位置,我時常得這樣翻來覆去的比較兩方。
有時候,我也會自問,人一生中,必定得定義自己的家鄉嗎?
近幾年我常常聽到「鄉土」這個名詞,無論是在國文課提到曾經風靡一時的鄉土文學,又或是在社會課裡學到要愛護鄉土。然我的生活何其複雜,在城市與城市之間、角色與身分的轉換間,我真的有辦法清晰的定義出所謂「鄉土」究竟在何方嗎?
對我來說,花蓮是安心的地方,像從小到大的一個玩偶,也許不起眼甚至褪了色,在嶄新的臥室裡顯得格格不入,但沒了他,與之連結的記憶好像也一同消失了。宜蘭呢?我和那個總是多雨的、差點要去生活的城市並不熟悉,記憶裡的片段都有模糊柔光的濾鏡,然而我的父母弟妹全都待在這裡,生命中的部分記憶也和那個小小的家有關,是我童年儲藏地之一。
何為鄉,何為土?我想,擁有記憶連結的地方,即是鄉土。
所以,我猜你不會介意我這麼說:宜蘭不是我的家,它是一台精緻的變頻冷氣。縱然如此,我想自始至終,它都是我不可定義,亦不可分割的一部份。
宜蘭家的洗碗槽前面有一扇窗戶,不大,卻足夠把城市的一隅圈在四四方方的框裡。有時候吃完午飯,家人去睡午覺,我就在正中午暖和的陽光裡吹著冷氣,洗碗清理。
此時空間裡只剩下水擊打到水槽底部的刷啦聲,還有海綿擠出泡泡再與光滑的盤子表面摩擦的聲響。斜後方的冷氣溫度調整到舒適的二十五度左右,亮著綠燈在我身後靜默的運作,扇葉緩緩降下,再慢慢地升起,送來涼風。我在沖水的空隙抬起頭,看著窗外來來往往的車輛,還有更遠的那方、百貨公司裡亮起的精緻燈光。
明亮的日光下,涼風陣陣,剛洗好的碗盤被照得發亮。我與那檯變頻冷氣都悄然無聲,我期待有那麼一天,不必探問鄉土,我也能夠清楚找到家的定義。